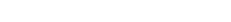匠心独具之作,“教”“学”两宜之书
2010/05/25
如今国内的图书市场,说教材(当然还要加上所谓“教辅”之类)占据大半壁江山,恐怕并不为过。其中外语类(特别是英语)的各种教材、教辅更是铺天盖地,这在全世界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观。虽说对林林总总的教材,人人(校校)都可以各选所需,但是以鄙见,终究是平庸之作居多,上乘作品比较难觅。这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编写教材的庞大队伍中,一流学者真正自始至终地亲自操笔动键者寡。不知有多少教材都是临时应命的集体班子,通过拉大旗作虎皮,赶时间促进度地劳作而最终托出的“拼盘”。说得尖锐一点,时下教材市场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我国教育领域里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现象的一个缩影。
尽管教材编写的大环境并不如人意,但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外文类翻译类教材中还是偶有精品闪现。最近笔者浏览到王宏印教授编撰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3月;以下简称《典籍英译》)时,眼睛为之一亮,颇有遇见“万绿众中一点红”的感觉。
一般来说,一本好的教材首先要做到两点:一是告诉读者或使用者一个明确的编写理念,二是教材围绕基础知识传输与基本技能训练进行有条理的谋篇。这两点《典籍英译》的编写者一开始在其绪论部份就叙述得很清楚:它是专门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而编写,以提高学生典籍英译的实际能力为出发点与归宿点。细读该书绪论会发现,虽然讲的是一本教材谋篇的方方面面,包括典籍英译的若干重要原则与总体策略,但透过表层的文字让人感受到的更是一种叠加的厚重感: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中国文字的厚重、中国典籍份量的厚重,最后当然是担当典籍翻译工作者责任的厚重。这些都隐约在起始阶段告诉读者:矢志于典籍翻译者自己得要变得厚重才行。推开这一扇扇厚重之门之后,我看到了或者说是发见了《典籍英译》的三个特色。
一、《典籍英译》有一个匠心独具的编纂构架。中国的典籍浩如烟海,经史子集单就书目排列就是煌煌巨册。一本教材如何能以最简练的方式将典籍(翻译)归类是一大难题。本书的编撰者以二十四讲(让人联想中国“二十四史”亦未尝可知)标题,分类十分清晰别致,且都以四字结构冠之,阅之易过目成诵,读之可体会几许余韵。没有对中国典籍有深广了解者,没有对历代文苑有大量涉猎者,没有高屋建瓴,能收宏观气象于微观表述之能力者,不能成此事。一般教材中的目录展现很少有如此精彩夺目的设计。
二、《典籍英译》体现出编撰者在其研究领域中长期的学识积淀。依我之见,教材有两种编写方式。第一种方式,也是最普遍的方式,就是把收集起来的资料整理一番,按一定的思路,编写成一册书。这个过程主要是“编”贯穿始终。从这个意义上讲,编主要指对现成的原料进行利用或加工。这个过程也许也能制作出不错的教材,但终究难产生有个性、有鲜明特色的教材。第二种方式,就是“研编”。在“编”字前面加一个“研”字便使教材的编写产生质的变化或展现出质的飞跃。换言之,要编纂一本质量上乘的教材,首先要有对相关的课目或题目进行研究的经历与成果,而这种研究又往往体现在一位或几位学者长期的学术专攻之上。坊间大量教材书本之所以显得平庸乏味,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它们都是“只编不研”或“有编无研”的结果。没有相关研究领域的长期浸润,没有较丰富厚实的学识积淀,“研编”教材就是一句空话。浏览《典籍英译》给我的一个强烈印象是,编撰者本人是一位沉得住气,奈得住寂寞,孜孜矻矻,长年专致于典籍及其英译领域,恐怕连旦晚乐趣均在其中的学者。教材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书中大量而详细且又“颇为读者计”(reader-friendly)的注释。编纂者如没有广博的阅览,没有大量的读书笔记,没有相当的自撰文著作基础,书中那些既可读而又极具信息量的注释条目是不可想象的。只要细细品味这本教材,读者恐不难感悟到这一点。
三、《典籍英译》一册在手,“教”“学”两宜。众所周知,人们购买、获取一本教材可能并不只是为了在课堂上使用,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为了自学或作为一种课外的阅读物而放上私人书架。编写教材的人因此不仅要想到课堂的情况与条件,也要考虑到课堂之外广大使用者的实际需要。显然,一本好的教材同时还应当是一本可供自学的书本。在这一点上《典籍英译》可称得上是一个范例。首先,它以简洁的文字描述了中华典籍的概貌及主要内容,给读者提供了一种清晰的认识中华典籍的轮廓线。即便是不涉及其英译领域的读者也能受益。其次,它结合实际译例,较为务实地在各个侧面与各个层次探讨了典籍英译的原则与技术处理。此外,使用者会发现,书中大多数的翻译问题讨论都附有参考或较理想的译文,供读者赏析。而独独在每课的练习部分不提供任何参考答案。这种做法一反同类教材的规则,但却也是编者的一个高明之处。现在国内编教材似有一种处处为使用者着想的过分周全的倾向。我以为,一本翻译教材若处处让学翻译的人“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样的教材最后的结果恐怕反而不会让人“留恋”。应当说,为练习提供相关的参考译文对《典籍英译》编纂者来说是一件不难的事,而编纂者故意留下一处空白,估计是要营造一种“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效果,弦外之音可能是:“我前面已经讲得够多,现在轮到学生自己来解决具体的翻译问题了。你行不行,试一试吧。”当然,学生在动脑筋端出自己的译文来的同时,也可以去查找相关的译文,即便是能快速“百度”到手,也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因为大凡经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或搜索到的知识或信息,总会更加难忘。练习留下一处答案的空白,从而将学生引入一个动脑动手的过程,而恰恰是这个过程对学习翻译的人而言意义重要,不可或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典籍英译》书后所附“中国历代文化要籍篇目(汉英对照)”涉及近六百个题(篇)目,无论对教师、对学生、亦或是对自学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教师而言,可以在这个长长的篇目里进一步发掘出教学的补充材料;对于学生而言,可以在如此丰富的资料库中寻觅自己更感兴趣的文章著作来满足课后阅读之需;对于自学者而言,则可以随时“出河入江海”,在典籍及其英译的广阔水域自由泛舟。
本文作者: 何刚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系系主任,兼任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